
枝头消息
枝头漫出鹅黄,很嫩,似乎吹弹即破。它们都蜷缩着,像是握住的拳头,还要一点时间,随着越发上升的气温,渐渐打开它的容颜。这是多么有诗意的色泽啊,很隐含、阴柔,同时又有一缕开张之气正待散发。刚刚好——我欣赏的正是这种欣赏态。
我是比较关注节气的人,这和当过农民有关,虽然最终弃农进城,节气的特征还是让我深刻记取。我会发现节气到来的这一天的确有许多不同,有时很微弱,不易捉摸,我还是会从一些景物、植物上挑出来,相应地做一些应和。老百姓觉得最简单有效的就是食补,使人在这一天里安然度过。时间在人的眼中,看起来都是一样的,无形无色,一日连着一日,匆匆而过,没有茬口。总是会在一些时间点,在这个点上,时间被格外注视,立夏了,立冬了,当放则放,当敛则敛。适时顺生,说的就是先从情绪上遵从,然后是肢体。如果从季节上划分,立秋之前都属于情调高涨时节,就连那些细微的鸣虫,肉眼看不到,却积极地发出声响,不愿停歇。在这个时段,什么都是向上的、开张的。我动手批改几个小青年的随笔,文辞不能说不顺畅,就是写得太华丽了,让人阅读中感到腻味。我原本想提笔叉掉它一堆词藻,使它变得质朴素淡一些。才下笔就停住了,自觉不妥。在这个年龄段,恍如初夏,无论是一个人的情怀,还是情怀之下的笔调,都是蓬勃不可遏,他们的表达,也就更充足和饱满,饰而无节。如果不是这样,反而辜负了此时的性情。
我与他们不一样,已经走过夏季,是秋季中人了,把笔行文,不知不觉地由丰缛华丽转为素淡,像一株删繁就简的三秋树。古人说得好:“后生好风花,老大即厌之”,我现在正是这个样子,想着如何在笔调上能渐渐贴近逸品,如果如愿,那真是太好了。可是难的是不能强求,只能自然而然,也许达到了,也许根本达不到,成为一辈子的牵挂。“逸”最早是对人品而言的,孔夫子就提到伯夷和叔齐,兄弟俩隐居于首阳山,不食周粟而死。大概要有隐士情怀的人,才有可能担当起逸的称号。我是很现实的人,不愿淡出红尘,入世越深,越是热爱尘世,对生活中的某些需求还表现得很有兴致,譬如美食——这是多么好的一份享受啊,孰可舍之?至多,一个人就是以入世之念,做一些雅致之事,如此而已。我没有太多的个人兴趣,像一个人站在呼呼的秋风里,有许多热情、愿望都被吹散了,剩下那些比较实在的成分。以前我在笔墨滋润中是做加法的,怕欣赏者看不懂来问我,还得解释半天。现在我则大做减法了,像一个园林管理者,大刀阔斧,删节枝条,把那些伸张的、绵密的、叠加的悉数削减。至于再来欣赏的人能否领会,我就全然不去考虑了。如果一个进入秋季的人还在追逐着繁缛艳丽,自己都会骂自己浅薄。尽管动不动就征引弘一法师来做逸的代表,但说到底他的人生对于常人而言根本没有普遍性,也不值得仿效。普通的生活是排斥这种极端的,即便有人仿效,也会在这样的环境下变形失真成为一个怪物。我觉得比较可靠的是更多阅读一些民间之作,里边蕴藏着边缘生存中人的人格、情调,在边缘习惯了,未曾有进入中心地带的念头,只是循着晴耕雨读的传说程序,素淡百年。这样比较真实的日子,给我的引导也比较可靠。
朋友们送给我几幅汉砖拓片。本来我只对墨拓怀有兴趣,以为黑白二色对比最有利,朱拓不免过于渲染。直到最近才有了转变,看到了朱红把销蚀风化的那一部分展示得那么沧桑。有时我就这么认为,古人手上的技巧并没有那么高明,也没有那么多滋味可品,笔下肯定也有一些啰啰嗦嗦的东西,就像汉大赋那样,毫不例外地来一番膏泽浮华——似乎一个有才华的人,都要以此显示一下才气,不知不觉就走过头了。后来,这些石刻砖刻置于时光之下,风沙往来,磨洗无休,那些显示才气的笔调,长的、露的、尖的、密的,百年千年,已经变成短的、敛的、钝的、疏的,变得有味道了。更多的人不喜欢这种删减,观赏时颇觉吃力——如果一个人只是对春日表示好感,始终浸泡在春日的汁液里,对个人的体验来说,显然是一种缺陷。
南方逐渐成了冬日越来越短的场域。曾经御寒的皮衣,已经闲挂在衣柜中多年。冷,这种让人肌肤异样的感觉,哆嗦的、发抖的、起鸡皮疙瘩的,不能说没有,却也淡去了很多。冬日不冷,说起来是轮回中的一种缺憾——不是四季匀称,而是以很大的偏差出现。它到来的时候,人们还穿着短袖短裙行走在喧闹的街市。除了服饰的错位,人的神情、举止,也全然不是这个季节所有。在肢体感受不到冬日的严寒时,一定是天道运行中有什么被阻止了、拖延了,使它迟迟不能来到我们的跟前,让我们切身感受。“天行健”,古人就是这么说的,没有谁对此产生怀疑,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的行踪,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握它的玄机。现在我们感知的,只是一些琐屑,一些小秘密泄露出来了——夏日比以前炎热得很。得出这个结论的大多是中年人,他们在空调的房间里,温度很低了,心头上还是烦躁得不行,这是机器所无法调节的。这个季节无节制地延伸了,让人很不舒服,它是属于张扬的、放纵的。看看南方的这些植物纵横伸展毫不敛约,你就清楚了。
树犹如此,人何以堪。就从我这个谋生的专业来说,那么柔软的毛羽制成的笔,居然写不出简净、简静的字来,更是难以捕捉到萧然、澹然的气味。就像弹琴,总是想在大庭广众里弹,弹给别人听,却不想幽篁独坐,弹给高山流水听,弹给自个听。
我想,问题就出在这里。

水汪汪的眼
对于深度的感受,我不是从书本开始的——一个不谙世事的孩童,很难领会数字给予的启蒙,譬如我们身处海平面多少米。我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地发现,成年后对于深度的认识,都要缘于孩童时代的亲眼所见。可以肯定指出,家园中曾经有过三眼汪汪的古井,如同三枚饱满滋润的水印子,钤盖在我敏感的皮肤上。观察着疏朗的枝叶向上生长的时候,对于古井低于人们行走的平面,我是油然产生奇怪的——既然向下发掘可以获得清亮的井水,那么,一定也会有很多未知的宝藏隐匿。多雨潮湿的地方啊,掘一眼井不算难事,可本意真是如此吗?我会觉得在这个家园里,掘地三尺另有企图,最终以一泓清泉的涌出作为回报。随着这些不知哪个朝代掘出的水井存世,井的周遭理所当然成了果林和菜园——井的延续改造了生活的面目,比掘出其他宝藏都清纯和透彻。井的出现使我对于深度有了抚摸的可能。间接地通过井绳,与深井接触。平静的水面,随着邻里结伴汲水,三四个小木桶此落彼起,烂银子似的荡漾波光。甚至在早睡的梦里,还能听到大人们借着洁白的月色浇灌、木桶击水或者桶帮与井壁磕碰的声响。朴素的温馨之夜,在清流的泼洒中走进安宁。一眼古井,经过漫长时日的打磨,已经泰然地与人亲和,不需要后人特意花费心机护理,只管使用便是。这也让人们对古井的牵挂最少,似乎前人的一次性劳动,后人得以永享安逸。对于轻松地享用,自然削弱了古井的重要——人的本性通常如此,譬如那些会讨会要咋呼不休的人,往往得到满足;而斯文缄默者,被人淡忘。在我那时学会的几个成语里,都是对井的不敬——井底之蛙、坐井观天,贬低的口吻里,分明涉及了井的固有状态,它的狭窄如“眼”,缺乏闳大的格局和开阔的气派,由此受到牵连。只有与井为邻的人才知道,古井的周围远比其他地方翠绿和润泽,有一缕缕草浆汁水的生生气息在井栏边无声地漾开;夏日里干渴的黄蜂和蜾蠃会结伴而来,伏在井沿凹下的水渍里。没有人去追问古井的来源,对于清亮照人的水和井内黑暗下去的视线,即便联想纷起,却没有一个人表示贪欲——共同拥有,人们的心态大都平静得如同井内之水。
区分新井和古井的差别是轻易的。新井内被砌起的石条全是崭新和锐利,白生生的茬口流露着火气,动荡的木桶不小心被磕碰,绳索被磨砺,马上露出伤痕。新井的水不时涌动着,水色浑浊,携带着土腥味。掘井人需要有足够的耐性等待清澈,每日汲出大量的水用于浇灌,期望浊去清来。不须太久,新井躁动的情绪被净化如一面不动的镜子,风吹不到,皱纹不生。井水的清冽、甘甜,传出后,来来往往的人就多了起来。时间慢慢地流过,井水总停留在一个水平面上,从未见少。“取之无尽,用之不竭”,记得小学老师把这八个字赋予了一个伟大的思想。我脑子一闪而过的,是老家那几眼黑洞洞的水井,这无疑是最感性和具体的。我甚至想,一些用语,如果乐于迎合思想和主义,对于涉世不深的少年,领会也许失之千里万里。完全可以用身旁的、日常的材料,大大缩短领会的长度——漫无边际地撕扯,只能让人无奈。至少,你感到诚惶诚恐。一切认识都毋须安排,要刻在头脑里剜却不去的,只能靠自己在岁月行走中获得的某些机缘。它自然而然地进入,比灌输的更不易风化。时日在井底下流失。当年锋棱锐利已经成为钝拙,曾经崭新的色泽变得泛黄,一些黧黑的苔藓,星星点点地附在井壁上,让人一眼望下去,发出井已老矣的感叹。冬温夏凉,井水在浑然无声的节候里默契转换。这样的井,是苍天幽深的眼神,水汪汪地穿透一切天机世相。水与水是不可相比的,波来波往、潮起潮落,流动的水是时间的一种表征,印证着时间的旅程。井水恰恰相反,一汪地静止索默,涵养着安宁,让人觉察不出它的意图。这也是古井难以枯竭也不溢涨的缘由,让人体验着静止的微妙——掘井之前,这口井的命数如何,是无从意料的,只能掘下去,这口井的个性才会显露。井和主人,只能靠机缘产生联系,那种掘井不成反而掘出了兵马俑的失败例子,只能归结为人与井没有缘分。
不能如愿的井让人难堪。当初那位手执罗盘看风水的江湖术士已经走远,掘到底才知道问题来了。有的井水量涓滴;有的则过于充沛,溢出不止;还有的不可食用。对于地下的奥秘,人所知之甚少,井下结构令人一筹莫展。动土之前据说要焚香敬拜的,这些对土地虔诚的人,重视这一道心灵的手续。揭破与水一层之隔的土皮,生命就汩汩而出了。泉眼的太旺与不足都是祸害,过程显然被浪费了。对于目的性很强的人来说,有价值与否要看结果。一眼井让人失望了,必须果断地填埋。掘出来的土才见到阳光,又匆匆返回潮湿的地下,堆挤压实。这时主人庆幸的是,好似一个出了瓶子的魔鬼,又被计谋引回一个生命在瞬间夭折。值得一提的是,直到现在仍然使用的井,它的生命质量令我们感佩莫名。对一眼井的要求,古人今人不会存有太大的差别,只是当时更多地作用于味觉,守一眼井,过一辈子。时光就是在变化中展开的,对于流逝不已中存在的一眼简陋的井,成了今日审美的良好向导。
如果不是有意地填埋,一眼井的年龄要远远超过了一个人、一个时代。深邃的井让人想起同样长久的大树,一个向下延伸,一个朝上生长。巨大的树干令人联系浑圆的井口,笔直的井如同直入云天的树干。井和树在不同的两极里素来默不出声,如果不是雨点落入井内,或者风掀动枝叶,安静是它的共同的语言。干枯的井会令人想起干枯的树干,意味着生命已经走远,只是残骸遗留。枯井的命运比枯树更为悲怆,它甚至就成了垃圾倾倒的场地,远远不如枯树在烈焰中焚化快慰。我们看到的是,城市的高楼越来越多,古井必然越来越少。许多高楼底下就是被填埋结实的井,发不出丝毫呜咽。城市里幸存的井,井沿上已很少汲水的印迹,人们只须两个指头轻轻捻动精致的水龙头,水便喷涌而出,不必弯腰揽绠作辛劳状,一种姿势从此消失。
曾经水井密集的村庄,大片大片地迁移走了。时代的变化之一就是人不安地移动。整个村庄搬得彻底干净,车运马驮,手提肩挑,甚至一些破烂用具,也因为车厢尚有些许空隙,也登上了旅程。在搬不动的物品里,井是最典型的,没有谁能把它移走。是人遗弃了井,还是井背离了人?当人们在新的居所,品着茶,觉出口味不对,才会想起丢在荒村中的井如何甘美,想起曾经过往的日子,想起井沿边的许多故事。不需特地设置悬念,一口与自己的童年、少年每日相伴的古井,那种清新和华滋,连同水汪汪的神秘,已经沁入了体内,纵使后来远走高飞,异域的风云蓄意介入并想取代昔日的痕迹,还真难成功。怀乡的主题如新月一般静静升起,也就是从不变的古井开始吧。不变的古井和多变的世相,不变意示着被封存、浓缩,在大寂寞中延伸、传递,使藏在幽深中的内容更值得寻绎。爱迁徙的人与移不动的井,如长风之于古树,不能互相厮守是一种必然。只能这么去面对了,当一眼古井孤零地停留在荒村里,倒映着孤月,它的凄美将使我们更加怜爱。
那些对于古井,不,就是对于一般的井也一无所知的少年,和那些曾经享受着汲绠之乐的少年相比,体验中肯定缺失了一个空间。一定会有一些人,在拨弄着便利的水龙头时,会在自己回眸的角度里,看到地下的潜流正在深处发出渴望的冲动,期待着涌出,重新成为生活的甘霖———我们所说的美感,一口井也足够赐予我们的了。

注:本文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,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,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,请立即后台留言通知我们,情况属实,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,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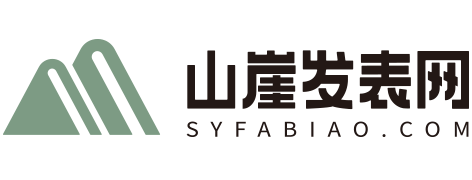
发表评论